
在看了几遍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后,我又认真阅读了斯蒂芬金的小说。本文内容主要参考了小说。
肖申克既是监狱,也是人生的象征和社会的隐喻,这一点,作者借故事的讲述者瑞德明确表示:
“我把监狱描绘成外面社会的缩影”。
那么,肖申克所隐喻的社会,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?一言以蔽之,就是一个处处体制化的社会。
1
“体制”可理解为包括某种规则、习惯、意识和氛围的环境,体制化通常指一种按部就班的生活,人们生活在其间,只能按照固定的模式行事,起初只是一种外在约束,慢慢地人们适应这种约束,最后人们离不开这种约束。体制化意味着对权威的服从,对自由的排斥。
根据百度百科释义,因为人对一种事物的依赖是出自自己的精神思维以及习惯,而在跳出原有的限制之外后,人们本能的反应是想在新的体制内寻找旧的体制拘束。就和一个方形在大的方形内可以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,但如果大的环境变成了圆形,那么方形就开始以自己的形态去配合圆形,这是不可能的事,而最终方形会心身力竭,悲剧就会这样的发生。
但如果方形将自己的容积变大,或者变小,它未必在圆形内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,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习惯性,而这种习惯性就是体制化。
体制化不是自然的产物,而是社会的产物,它的根源是意识形态。
2
体制化作为社会产物,如何使个体体制化呢?小说中瑞德的一段独白做了形象描述:
“我曾经试图描述过,逐渐为监狱体制所制约是什么样的情况。起先,你无法忍受被四面墙困住的感觉,然后你逐渐可以忍受这种生活,进而接受这种生活……接下来,当你的身心都逐渐调整适应后,你甚至开始喜欢这种生活了、什么时候可以吃饭,什么时候可以写信,什么时候可以抽烟,全都规定得好好的。
如果你在洗衣房或车牌工厂工作,每个小时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上厕所,而且每个人轮流去厕所的时间都是排定的。三十五年来,我上厕所的时间是每当分针走到二十五的时候,经过三十五年后,我只有在那个时间才会想上厕所:每小时整点过后二十五分。如果我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没办法上厕所,那么过了五分钟后,我的尿意或便意就会消失,直到下个钟头时钟的分针再度指在二十五分时,才会想上厕所。”
这段描述虽有带有文学夸张,却也直击体制化的核心。它表明体制化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漫长的驯化过程。人一旦被体制化,就近乎本能地过上循规蹈矩的生活,不敢质疑批判,不敢越雷池半步。体制化的个体一旦被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,就变得格格不入。我们从瑞德假释后适应新世界的过程,就能看到体制化根深蒂固的影响:
“我一时之间很难适应这一切,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,就拿女人来说吧。近四十年的牢狱生涯,我几乎已经忘记女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。突然之间,我工作的地方充满了女人——老女人、怀孕的女人(T恤上有个箭头往下指着肚子,一行大字写着:‘小宝宝在这儿’),以及骨瘦如柴不穿胸罩、乳头隐隐凸出的女人(在我入狱服刑之前,女人如果像这样穿着打扮,会被当街逮捕,以为她是神经病)等形形色色的女人,我发现自己走在街上常常忍不住起生理反应,只有在心里暗暗诅咒自己是脏老头。
上厕所是另一件我不能适应的事。当我想上厕所的时候(而且我每次都是在整点过后二十五分想上厕所),我老是有一股强烈的冲动,想去请求上司准我上厕所,我每次都忍得很辛苦才没有这么做,心里晓得在这个光明的外面世界里,想上厕所的话,随时都可以去。关在牢中多年后,每次上厕所都要先向离得最近的警卫报告,一旦疏忽就要关两天禁闭,因此出狱后,尽管知道不必再事事报告,但心里知道是一回事,要完全适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”
假释后明明获得了自由,瑞德却在很长时间连上厕所都会习惯性地请求上司准许,这正是体制化的一大危害:当体制强加的东西消失后,它们依然在你身上阴魂不散。小说中提到的波顿和他的鸽子“杰克”,也是被体制附身的典型。瑞德讲到:
“我认识一个叫波顿的家伙,他在牢房里养了一只鸽子。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,当他们放他出来走走时,他都带着这只鸽子。他叫鸽子‘杰克’。
波顿在出狱前一天,也放杰克自由,杰克立刻姿态漂亮地飞走了。但是在波顿离开我们这个快乐小家庭一个星期之后,有个朋友把我带到运动场角落,波顿过去老爱在那里晃来晃去。有只小鸟像一堆脏床单般软趴趴地瘫在那里,看起来饿坏了。我的朋友说:‘那是不是杰克啊?’没错,是杰克,那只鸽子像粪土一样躺在那儿。”
透过波顿的小鸟,我们可以发现,所谓体制化,就是一个牢笼,长期生活在牢笼中,人的本能极大地退化,一旦被放到一个自由的环境中,就变得无所适从,最终不免被世界所淘汰。这种现象并非个例,它具有普遍性。
3
之前有位高铁列车员被开除后,撒泼式地哭诉:“自己年龄太大了,除了高铁列车员的工作,什么也干不了。”说明她也被体制化了。其实,何止某些人,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被体制化了,只是有的人中毒太深,以致于完全不能适应体制外的世界;有的人体制化的程度轻一点,所以即使离开了旧体制,也能慢慢适应新体制。
小说还讲到布鲁克的遭遇,他也是典型的体制化的受害者。
“布鲁克是在柯立芝还在当总统的时候,赌输后失手杀了妻女而被关进来。他在一九五二年获得假释。像往常一样,政府绝不会在他还对社会有一点用处的时候放他出去。当罹患关节炎的布鲁克穿着波兰西装和法国皮鞋,蹒跚步出肖申克大门时,已经六十八岁高龄了。他一手拿着假释文件,一手拿着灰狗长途汽车车票,边走边哭。
几十年来,肖申克已经变成他的整个世界,在布鲁克眼中,墙外的世界实在太可怕了、就好像迷信的十五世纪水手面对着大西洋时一样害怕。
在狱中,布鲁克是个重要人物,他是图书馆管理员,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。如果他到外面的图书馆求职的话,不要说图书馆不会用他,他很可能连借书证都申请不到。我听说他在一九五三年死于贫苦老人之家,比我估计的还多撑了半年。是呀,政府还蛮会报仇的:他们把他训练得习惯了这个粪坑之后,又把他扔了出去。”
几十年的监狱生活,布鲁克早已习惯了周遭的一切,不仅意识不到体制化的危害,还喜欢上了这种生活,因为在这里,他存在感十足,而到了外面的世界,他就变得一无是处。
瑞德也有这种感受,当安迪希望他出狱后为他搞定生活和工作所需的一切时,他感到自己根本没法胜任。
“我沉吟良久,当时我想到的最大困难,居然不是我们不过是在监狱的小运动场上痴人说梦,还有武装警卫居高临下监视着我们。‘我没办法:我说,我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。我已经变成所谓体制化的人了。在这儿我是那个可以替你弄到东西的人,出去以后,如果你要海报、锤子或什么特别的唱片,只需查工商分类电话簿就可以。在这里,我就是他妈的工商分类电话簿,出去了以后,我不知道从何开始,或如何开始。”
瑞德其实不像他想得这么糟糕,他走出监狱依然可以适应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,但是,对不确定世界的过分恐惧束缚住了他的想象。
4
在长久的体制化后,对于那些总是尝试越狱(也就是极力冲破体制牢笼)的犯人又怎样呢?多半也在劫难逃,因为奴在心者,身上枷锁去掉后,依然跑得过和尚跑不了庙。这也正是体制化最可怕之处。瑞德对肖申克中这种现象洞若观火:
“……比较认真策划的越狱行动大概只有六十件,其中包括一九三七年的‘大逃亡’,那是我入狱前一年发生的事情。当时肖申克正在盖新的行政大楼,有十四名囚犯从没有锁好的仓库中拿了施工的工具,越狱逃跑。整个缅因州南部都因为这十四个‘顽强的罪犯’陷入恐慌,但其实这十四个人大都吓得半死,完全不知该往哪儿逃,就好像误闯公路的野兔,被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车头灯一照,就动弹不得。结果,十四个犯人没有一个真正逃脱,有两个人被枪射死——但他们是死在老百姓的枪下,而不是被警官或监狱警卫逮着,没有一个人成功逃脱。
从一九三八年我入狱以来,到安迪第一次和我提到齐华坦尼荷那天为止,究竟有多少人逃离肖申克?把我和韩利听说的加起来,大概十个左右只有十个人彻彻底底逃脱了。虽然我没有办法确定,但是我猜十个人当中至少有五个人目前在其他监狱服刑。因为一个人的确会受到监狱环境制约,当你剥夺了某人的自由、教他如何在牢里生存后,他似乎就失去了多面思考的能力,变得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野免,看着迎面而来、快撞上它的卡车灯光,却僵在那里动弹不得。”
这些越狱的犯人以为逃出了肖申克就能获得自由,殊不知,在丧失了追求自由的能力后,在飞翔的翅膀被折断后,所谓跳出牢笼,不过是跳出一个牢笼又钻进另一个牢笼。
5
但是,人真的注定要被体制驯服吗?在肖申克监狱中,安迪正是那个从始至终未被驯化的人,他是真正“单纯”的自由人。他就是那种注定要飞翔的鸟儿,正如瑞德的独白:
“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,它们的羽毛太鲜明,歌声太甜美、也太狂野了,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,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,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。”
当然,安迪·杜佛尼的自由之路并不容易,体制的牢笼给他的自由设置了重重障碍,“姊妹”的暴力骚扰、动辄得咎的禁闭、虚伪而蛮横的典狱长的专制、越狱时恶劣的管道……每一个障碍都可能致人死地或让人永不得翻身。但他从不曾屈服,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活没有磨平他渴望自由和救赎的棱角,他的十英尺长的鹤嘴锄石锤始终在挖体制化的铜墙铁壁。在瑞德看来要六百年才能挖通地道,而安迪用二十七年(虽然也漫长)就越狱了。
尼采说“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何而活,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”,安迪正是这种为了心中的希望和自由而甘愿忍辱负重的人。
肖申克的监狱监禁了他的身体,却没有打垮他的希望和勇气。正如安迪所说:“世上有些地方,石墙是关不住的。在人的内心,有他们管不到的地方是完全属于你的。”安迪始终保持着未被体制化的清醒,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。所以就算他最后越狱失败,也是当之无愧的勇士。
最后借电影中安迪的一段告白,与大家共勉:
“如果你感到痛苦和不自由,我希望你心里有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,不要麻木,不要被同化,拼命成为一个有力量破釜沉舟的人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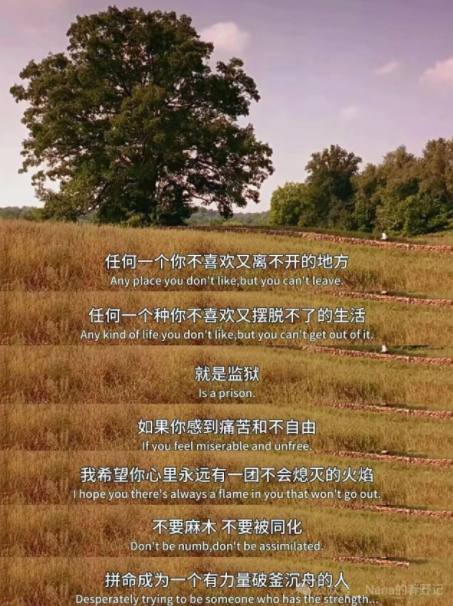
(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:读书人的精神家园。转载仅供学习交流,图文如有侵权,请来函删除。)